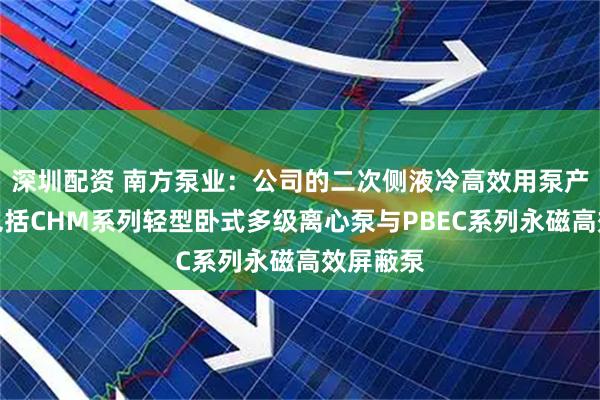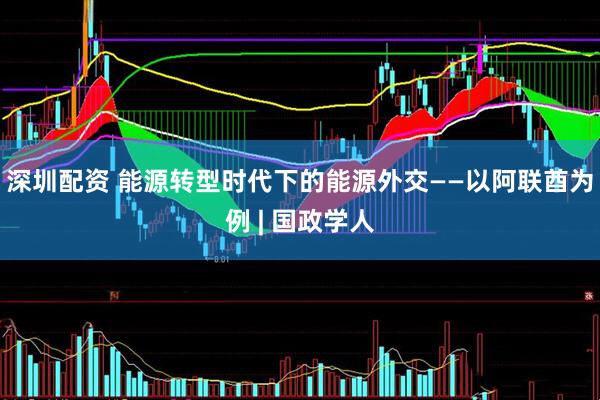
图片深圳配资
能源转型时代下的能源外交
图片
作者:Steven Griffiths,哈利法科学技术大学研发高级副总裁兼实践教授,阿联酋研究与发展委员会、迪拜未来能源委员会成员。
来源:Griffiths S. Energy diplomacy in a time of energy transition[J]. Energy Strategy Reviews, 2019, 26: 100386.
导读
受技术进步所带来的可再生能源生产成本下降、人们对气候变化的愈发重视等因素推动,以清洁能源为主要形式的能源转型,已经成为了未来能源发展的必然趋势。能源转型催生了包括能源生产者与消费者之间的权力关系变化等一系列的地缘政治影响,以沙特阿拉伯、伊拉克为代表的能源出口国的利益在这一转型过程中所受到的影响则更为直接。本文采用个案研究法,以作为碳氢化合物出口国、强调外交战略的阿联酋为具体案例,系统分析了阿联酋在能源转型时代下的能源外交战略,并以此提出能源出口国应发展特殊双边关系、重视软实力发挥、参与多边外交等见解与思考。
背景:能源转型与能源外交
能源转型
2017年,除大型水电外的可再生能源占全球新增发电量的61%;2015-2018年间,电动乘用车销量的年增长率每年保持在近60%。有鉴于此,彭博新能源财经(BNEF)通过预测指出,到2050年,可再生能源将占全球发电量的约64%,而发电量本身将增长近57%,达到38685太瓦时(TWh)。在运输部门,BNEF预计,到2040年,55%的新车销售和道路上33%的轻型车辆都将由电力驱动,加之车辆运输效率的提高,石油化工生产的需求将开始超过石油运输的需求。
尽管能源转型的趋势明显,但不可忽略的是,社会和政治动态是清洁能源技术被采用程度的关键决定因素。清洁能源的快速和显著扩散需要一个重视可持续性的强有力的全球能源治理体系。换而言之,薄弱的全球能源治理极有可能阻碍清洁能源技术的部署。
可再生能源的总量丰富性、部分能源类型(太阳能、风能)的强间歇性、对分配发电机会的提供和技术依赖等特征催生了地缘政治的两方面变化:一方面,能源生产者与消费者之间的权力关系将发生变化,能源组合方式由“能源资源稀缺+地理集中”的组合转变为“资源丰富+能源自给+电力联网”的组合;另一方面,电力作为能源载体的重要程度日益提升,使得“数字化”成为能源转型的关键组成部分,并进一步赋权于拥有先进数字技术的国家。
能源外交
尽管能源外交目前尚不存在一个明确的定义,但其旨在确保一个国家的能源安全,并促进与能源部门相关的商业机会,已经成为共识性内容。全球能源治理是大规模能源体系转型中最为重要的多边外交形式,其内涵包括在全球范围内确保能源供需安全、经济发展、国际安全、环境可持续性和良性国内治理。但由于能源所具有的特殊性,导致有限的能源治理概念形成了一种“主权悖论”(a paradox of sovereignty),即尽管能源市场的全球化在客观上削弱了各国对其自身的能源利益控制, 但由于各国未能采取具体行动,强有力的全球能源治理潜力仍未能得到发掘。
双边外交是两国之间直接进行外交接触的外交方式,既高效又灵活,因为参与方少、协调成本低,利益更容易达成一致。一旦建立双边外交关系,其在支持一个国家能源利益方面的有效性,则取决于一个国家能够与其同行建立的权力或影响力。在这方面,“软实力”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尽管拥有足够资源的国家可以通过“硬实力”胁迫或以支付代价的策略来成功实现能源转型,但大多数国家缺乏以硬实力实现其能源外交政策目标的物质资源;中国作为少数拥有大量经济及自然资源的国家,其也倾向于以“软实力”来获取能源利益。因此,考虑到信任和合作伙伴关系在能源关系中的重要性,作为软实力关键工具的双边外交对能源转型期间的国际关系至关重要。
海湾合作委员会的双边能源外交
海湾合作委员会面临的挑战
海湾合作委员会(Gulf Cooperation Council,GCC)国家历来可以获得廉价而丰富的天然气和石油供应以满足其国内能源需求,但近年来这种情况有所变化。虽然海湾合作委员会的石油储量仍然丰富,该地区约占已探明原油储量的30%,占全球石油出口的28%,但除卡塔尔外,所有海湾合作委员会国家的国内天然气产量都出现了短缺,无法满足日益增长的国内需求。受制于卡塔尔与沙特阿拉伯、巴林和阿联酋的政治分歧,海湾合作委员会国家正在寻求开发本国的天然气资源,以及部署包括核能和可再生能源在内的清洁能源,以尽可能低的成本实现国内能源安全。
在能源转型背景下,相较于国内能源安全,海湾合作委员会国家将其碳氢化合物资源货币化的需求则更为急迫。据相关研究指出,世界石油需求减少2.5%-10%将使海湾合作委员会国家的石油出口收入减少5%-40%,具体数值则取决于特定国家和全球石油需求减少的程度。石油收入的大幅减少将对海湾合作委员会国家的当前经济结构产生重大影响。对海湾合作委员会国家而言,其50%以上的财政收入都来自碳氢化合物出口,GDP的任何重大多样化举措也均基于碳氢化合物出口收入进行的投资和支出来支撑。
作为个体案例的阿联酋
阿联酋在能源转型时代下的能源外交行动主要聚焦于以下四个方面:
其一,重视与中国等亚洲国家的特殊外交关系。以中国为例,中国在阿联酋的外交关系上具有特殊地位。企业层面,中国已经成为阿布扎比国家石油公司(ADNOC)石油和天然气业务的主要参与者。如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不仅获得了ADNOC陆上和海上特许权的股份,ADNOC还在2018年7月向中国石油集团子公司BGP授予了一份价值16亿美元的陆上和海洋三维地震勘测合同等。阿联酋与中国间的关系亦在企业层面外深化。如穆巴达拉投资公司成立了阿联酋—中国联合投资基金,以投资于阿联酋和中国的资产——这一基金的成立,充分展示了海湾合作委员会与亚洲经济体之间的第二层战略合作,即联合投资和基础设施开发。
其二,将进军石化定位为碳氢化合物行业的关键突破点。ADNOC计划在2025年前投资450亿美元,将阿布扎比发展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综合炼油和石化综合体。此外,海外机会亦是阿联酋能源外交的一个关键方面,力求使阿联酋深度参与进各国的炼油和石化能力发展之中。如ADNOC在印度拟建的勒德纳吉里炼油和石化综合体中持有25%的股权;与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就中国对阿联酋石化和炼油厂的投资,以及阿联酋与中国对中国下游资产的联合投资进行了接洽等。
其三,整合同其他能源生产国的共同利益。将碳氢化合物资源货币化、重视亚洲下游市场是包括阿联酋在内的能源生产国的共同需求。基于此,阿联酋重点深化了同俄罗斯和沙特阿拉伯之间的双边关系。阿联酋与俄罗斯于2018年6月正式建立了战略双边伙伴关系,旨在促进两国间在石油、天然气和核能领域的共同利益;沙特阿拉伯方面,阿联酋和沙特阿拉伯成立了联合合作委员会,合作范围涵盖两国之间的“所有军事、政治、经济、贸易和文化领域”。
其四,重视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的合作发展。到2030年,人工智能可为阿联酋的GDP贡献高达960亿美元,到2035年可为阿联酋总增加值(GVA)贡献多达1820亿美元。此外,人工智能亦是能源部门数字化的核心,可以支持阿联酋整合可再生能源技术进入该国电力部门,创建智能交通系统,降低阿联酋石油生产成本,以提高该国石油出口的长期盈利能力。除阿联酋外,中国、日本、韩国、新加坡、印度等国也推出了各自的人工智能战略,为国际人工智能合作奠定了基础。然而,到目前为止,只有印度和中国正式与阿联酋就人工智能进行双边合作。因此,阿联酋需要扩大和深化其在人工智能领域的国际参与,特别是重视与中国在该领域的合作。
结论与建议
向主要以清洁和可再生能源为基础的全球能源系统过渡将产生重大的社会、政治和经济影响。多边外交将在决定这一过渡的最终规模和程度及其对具有共同利益的国家和组织集团的影响方面发挥关键作用,而双边能源外交则可以通过促进能源供需方面的外交关系,支持各国长期的能源安全和经济福祉。与其他海湾合作委员会国家类似,低碳能源转型使阿联酋的能源外交主要关注在将该国碳氢化合物资源货币化商机的开发上,并确保经济多样化,以减少对石油出口收入的依赖。基于这些考虑和本文提供的分析,双边能源外交需要在能源外交战略制定中被定位为“优先事项”。参考阿联酋案例研究得出的见解,本文作者提出以下外交政策建议:
其一,与能够在低碳能源转型期间提供战略利益的国家发展特殊双边关系。阿联酋已经与一些在能源和经济方面能够成为重要合作伙伴的国家建立了特殊战略双边关系,但仍可与在石化等关键增长领域拥有强大能力的国家建立额外的特殊关系。
其二,让外交部以外的主要国家利益攸关方参与促进特殊双边关系。特殊双边关系需要伙伴国和阿联酋政治领导人定期进行磋商。这些磋商包括阿联酋外交和国际合作部,但也应扩大到其他阿联酋负责能源、工业、环境和技术的部委。ADNOC和穆巴达拉等组织在双边能源外交中也发挥着重要的外交作用。
其三,发展和利用双边能源关系中的软实力。阿联酋通过穆巴达拉和其他阿联酋政府组织建立的多项双边投资关系,有效发挥了软实力。阿联酋-中国周的设立是对使用软实力的进一步努力,可以在其他关键双边关系中进行复制。
其四,开展双边合作,提升国家科技能力。数字化,尤其是人工智能,是所有行业先进技术发展的最关键领域之一。阿联酋与人工智能前沿国家,特别是中国的牢固双边关系,使人工智能合作成为一个重要机遇,将直接造福于该国的能源部门。
其五,参与多边外交,以作为对双边关系的补充。多边外交将继续对阿联酋在全球能源治理中获得发言权至关重要。这意味着,阿联酋目前与国际可再生能源机构、欧佩克和其他多边组织的强有力接触对全球能源对话至关重要。
词汇积累
renewable energy
可再生能源
bilateral diplomacy
双边外交
hydrocarbon
碳氢化合物
monetization
货币化
译者: 孙溶锴,国政学人编译员,吉林大学行政学院国际政治系博士研究生。
校对 | 王星澳 周谷子
审核 | 施榕
排版 | 李明仰
本文为公益分享,服务于科研教学,不代表本平台观点。如有疏漏,欢迎指正。
图片
本站仅提供存储服务,所有内容均由用户发布,如发现有害或侵权内容,请点击举报。辉煌优配配资提示:文章来自网络,不代表本站观点。